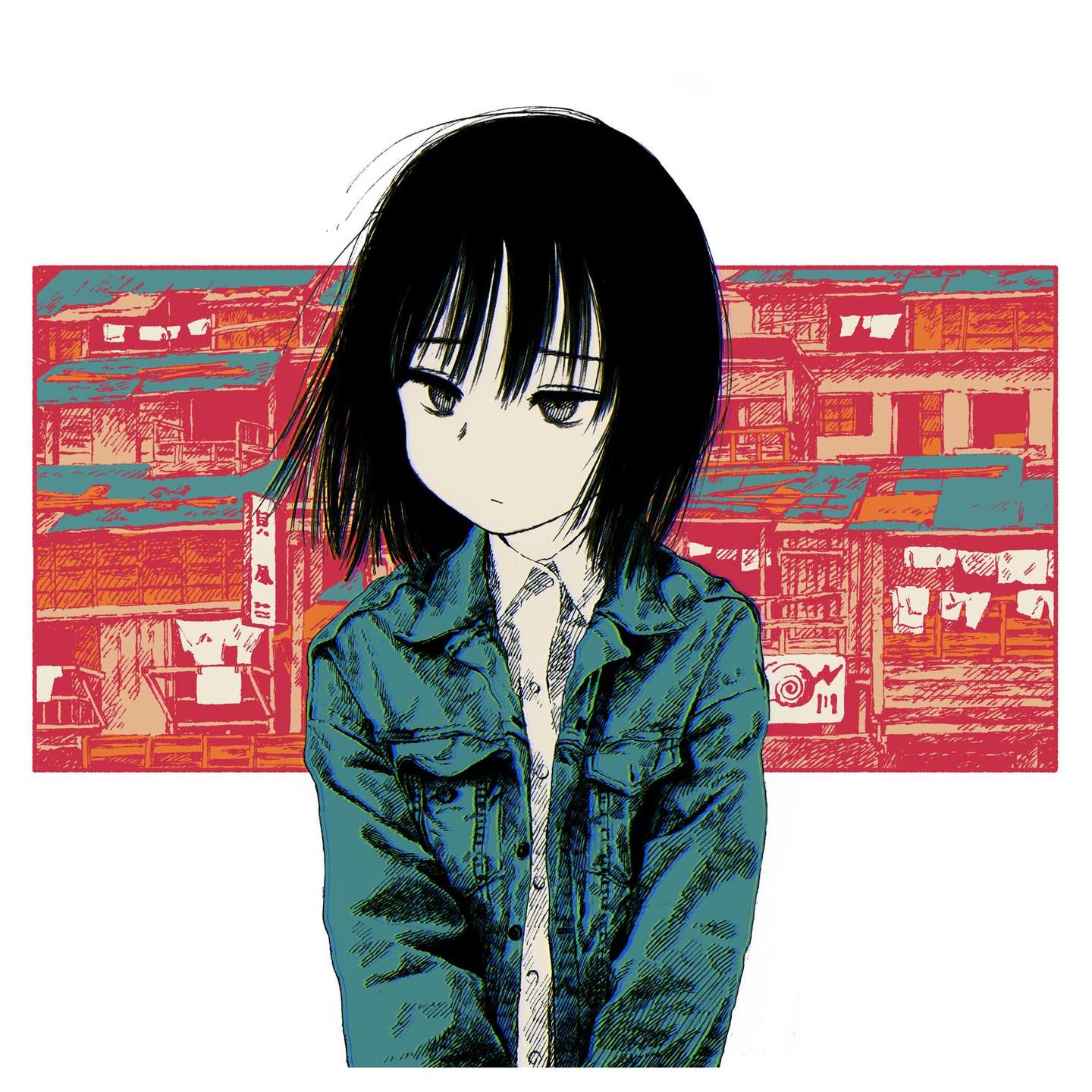type
status
date
slug
summary
tags
category
icon
password
fullWidth
fullWidth
根据上一期结尾列出的关键词,似乎得从“恋情”开启这一期的内容了。
先说一个可能会让大家比较震惊的事实:高中三年我单身的日子不超过五个月。
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爱情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并非必需品,可是在那种压抑的环境下追求这种不被“允许”的关系,也是当时的我最大限度地对抗环境的一个手段。而经过了和不同类型的人相恋、相处,我的爱情观在高中阶段得以逐渐形成,虽然可能依然不成熟,但的的确确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从完全不知道爱情为何物到对爱情有着自己的见解的过程。
整个高中一共有过三个的男朋友,最后都由于种种原因分道扬镳了。但我决定在这里只写其中的一位,理由是和其他两位相恋时我的恋爱观还处于萌芽阶段,似懂非懂的时候多少带有一些“尝鲜”和“跟风”的意味,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也显得格外局促。最重要的是与他们相恋的经历对于我人格的塑造几乎不产生影响,我写这个专栏的初衷在上一篇也提到了,是希望通过回忆一些高中生活的二三事去发掘自己人格中流失的部分,反思自己的变化并从中得到一些有用或者没有用的结论。因此我并不希望把它写成单纯的“风流史揭秘”,而是通过一些人物作为线索将一些与他们有关的事件串联起来,这样做也为我写下这篇的时候提供思路。
我决定着笔的那一位是我高中时期谈的最后一位。因为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性格,极端一点地讲,我从“焦虑型依恋人格”转变为“回避型依恋人格”一定程度上受了他的影响。经历过与他相处的过程,我性格中理性淡薄的成分得到提升,对于柏拉图式爱情的渴望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而是更偏向于逻辑性的要求;例如被某人吸引之后会从短暂的失控中迅速调整回来,思考这个人在哪些方面符合我对理想伴侣的要求。
接下来将以“小K”来称呼这位我高中时期的恋人。他高中的时候给自己取的英文名叫“Kasena",他觉得自己有着“风”的特质,kaze在日语里是风的意思,经过一番小变换就成了“Kasena"。和他初次相遇是某天晚上在学校艺术楼的琴房里。
上文提到,我从高二开始就频繁翘晚自修了。那天和往常一样溜出教室,却不幸地发现经常光顾的有钢琴的那个音乐教室被锁门了。我试图扒拉了一下窗户,是开着的。我熟练地环顾四周,确认周围无人之后敏捷地跳窗进去并迅速拉上窗户。舒了一口气,把弱音踏板扣上,坐下来弹琴,这样能确保琴声在关门关窗的情况下只有我一个人能听到。过了一会,我听到窗户被拉开的声响,一转头,窗帘竟然动了!我吓得原地弹起,觉得自己刚才翻窗进教室的时候一定是被老师发现了,完蛋。
我咽了一口口水试图平复心情,这时,窗帘后面徐徐探出一个脑袋。还好不是老师,而是一个戴黑框眼镜的男生。我对这位不速之客有印象,是另一个尖子班学数学竞赛的同学,从初中开始就有所耳闻这位尤其擅长数学,而且因为理科好加上会弹钢琴似乎还收获了一批“迷妹”。我和他都是提前批进的这所高中,入学前的暑假我学习过一段时间的物理竞赛(后来觉得学竞赛像赌注,没能出成绩还浪费了大量时间的情况大有所在,加之自己并不想过得太累,想把更多时间花在其他兴趣爱好上,就没有坚持学下去),他在隔壁教室上数学竞赛,走廊上和食堂见过不少次,因此当时我们算是互相认识但并不熟的同年级同学吧。
杵在原地不知所措了几秒钟,我招招手示意他跳进来,“门锁了我只能跳窗进来这里弹会儿琴,要不你也跳进来吧,不然很容易被老师发现的!”他很乐意地跳进来了。
“听说你也会弹钢琴欸——”我试图发起聊天破解尴尬。
“啊,是的。”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知道你会弹。”接着他补充道,“我看到你好几次都往艺术楼这边走而没去教室,就有点好奇,后来在外面听到你的琴声才知道你是来这里练琴的。”
“你偷听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太大声了我捂住了嘴,他被逗乐了笑了一下。“其实......其实我也没有在练琴啦,只是随便瞎弹的,呆在教室里实在是太闷了就跑来这里透透气。”我解释。
“不会被老师发现吗?”
“目前还没有被抓到过哦,我很小心的。”我拍拍胸脯。
“你刚才弹的旋律是自己写的吧。”他大概是通过我不断尝试不同的旋律走向时磕磕绊绊的琴声判断出来的。
“是的呀。”我有些不好意思,当时学校里并没有人知道我在创作音乐,属于是一个人偷偷地进行一项秘密活动。
“你好厉害,我觉得会即兴创作的人都很厉害,刚才的旋律很好听。”不知道是客套话还是他发自内心的夸赞,当时的我竟然有点被他的赞美触动到了,一直是一个人默默创作的自己不太敢也不好意思将一定会被视作“不务正业”的秘密活动告诉别人,因此能受到他的肯定对我而言是一件意外欣喜的事情。
“哪有哪有,这哪能算即兴创作啊。我只是在尝试怎样编排音符会让旋律变得好听,如果听到了让自己满意的组合我就记录下来,周末回家拿电脑写成曲子。”我解释道,“好几年没有练琴了,我的弹奏水平下降了太多,所以我更希望用软件里的乐器来演奏我写的曲子,做成音频文件上传到音乐平台上,这样大家都能听到......”
一旦聊到了感兴趣的话题,我的话匣子就被打开了。那天晚自修的时间,我和他坐在一张琴凳上,一边轮流弹琴,一边讨论怎样编排旋律才会使之动听,讨论自己喜欢的音乐风格和作曲家,讨论调性的情绪意味以及和声对于曲风的影响,虽然我们都是业余的钢琴爱好者,但并不妨碍我们对音乐有着自己的深层次见解。我们从钢琴和创作聊到学习、生活,当时被前任甩掉不久,处在自卑、自闭状态下,创作也瓶颈了的自己在一瞬间觉得遇到了知音,遇到了另一个极其相似又迥然不同的灵魂,一个可以同自己产生共鸣的灵魂。和他聊天的过程相当轻松愉快,许久以来一向对他人有些小心翼翼的我能完全敞开心扉,我恨不得将灵魂整个吐出来展现在他面前。
第一堂晚自修的下课铃响了,他说他当天的作业没有写完,第二堂晚自修只能回教室写作业。我说好。他问我明天相同的时间还能来这里找我吗,我很开心地答应了。接下来的一小段日子里,夜晚的钢琴教室不再只有我一个人,我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光变得更加快乐了一些。
不久之后期末考到来,许久没有认真学习的我还是靠着啃老本顺利地考了年段第三,他似乎也考得不错。然后就到了寒假,我们在QQ上保持联系,但见不到他的日子总感觉缺少了什么。这段时光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可称作“暧昧期”,但我不太愿意去这么定义,因为“暧昧”这个词显得目的性过于明确,对于当时爱情观偏向柏拉图式的我来说任何带有功利成分的说法都让我多少有点感到不适。虽然想不到更确切语句来描述,但不得不承认,在那段时光里我渐渐喜欢上他了。
寒假的某一天在QQ上聊天时,不知是谁开启的话题,渐渐聊到了对于理想伴侣的标准。我问他:“可以描述一下你的理想型吗?”原以为会收到长篇大论或者条目式的回复,结果他只回复了我短短一句话:“我的理想型是你。”我秒回:”好巧,我也喜欢你。”
四年之后再去回想和他最初恋爱的时光,记忆已经不能够连贯了。我依然记得,第一次约会时我一把就抓到娃娃的时候他夸我好厉害,但绝对是敷衍的成分大于真诚;我被章鱼小丸子烫到后味觉下线了好几天,当时我和他都被烫到了,口腔疼的不行,但想在对方面前维持矜持的形象双双不敢吱声,后来提起来的时候觉得很有趣;还有在教堂外牵手拍影子的合影,排队买鼓楼的麻花......
寒假的时候我写了一首歌,叫《风的旅人》,这是接触编曲以后第一次尝试使用多种乐器而不是单一的钢琴进行创作。虽然没有学习过除钢琴之外的乐器,我还是凭着自己积累了多年的乐感,一边参考学习其他歌曲一边在摸爬滚打和不断尝试中完成了它。最后我很高兴地将我的作品发给他听,他说动人的音乐要是能被演奏出来就好了。
我仔细想了想,这首音乐的主体乐器钢琴可以由我和小K完成,除此之外还有小提琴、长笛、大提琴、鼓和一些别的打击乐,可以去学校的管弦乐队问问是否有同学愿意加入。
夹带一下私货:风的旅人,这是这首歌在网易云音乐上的链接,如果有兴趣可以点开聆听一下。
是个很好的想法!我兴奋起来了,要是我的作品能被大家听到,或许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于是接下来的几天我奔走于各个班级的教室,询问会其他乐器的同学是否愿意加入我们一起演奏《风的旅人》。对于实现这个想法的强烈愿望让我克服和陌生同学交流的恐惧,我向他们说明我的意图和想法,再礼貌地征求许可,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觉得当时的自己很了不起,能不慌不忙、逻辑严密地表达诉求,现在的自己也不一定能做得到。
尽管被拒绝过几次,但大部分问过的同学都表示乐意加入我们。于是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我在学校里找齐了大小提琴手、鼓手、吉他手、长笛手、鼓手和打击乐手,即所有能够一起演奏完成这首音乐的同学。此外,吉他手的朋友是学校音乐社的社长,她听完我们的想法之后希望将这个器乐合奏节目作为社团节目在学校的艺术节上进行演出。我再高兴不过了,我完全没有想过我出于私心的想法竟然能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最后我们都加入了音乐社。
从那以后,晚自修期间的钢琴教室从两个人变成了一群人,大家请假的请假、翘课的翘课,汇聚在这里“排练节目”。由于筹备艺术节和比赛,管弦乐队的同学偶尔请假是可以得到允许的;当时艺术楼的其他教室也有在排练演出或者比赛的,因此路过的老师并没有太在意我们。虽然说来这钢琴教室的目的是“排练节目”,但更重要的是享受不被监管的自由。
渐渐的,那个钢琴教室成了我们的派对场所,一个可以谈恋爱、吃零食、看闲书、抄作业、甚至带手机打游戏,而不会被监管和问责的地方。大概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个原因,大家排练的积极性很高,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合乐演奏,效果相当不错。由于主要任务的完成度高,除了排练之外能做其他事情的时间也多了不少。我在那个教室借别人带来的闲书看,向鼓手学了点简单的动次打次,练琴累了的时候就打会儿鼓换换脑子,甚至在角落里找到了一个没人拉的二胡和一本教程,浅浅地自学了一下拉会了千本樱,虽然我的音准让这首歌听起来像鬼哭狼嚎(笑)。
那会儿社长向我们推荐了一部音乐剧,叫《摇滚莫扎特》。我们用钢琴教室自带的投影仪和大屏幕放,把小方凳拼成一张大床,大家坐的坐躺的躺,围在一起看。
法扎(法语版《摇滚莫扎特》)从各种意义上都破除了我对于音乐剧的刻板印象。本身对古典乐和美声并不感冒甚至觉得有些枯燥的我很少看音乐剧,但法扎确实震撼到了我,是第一部我能完整看下来并愿意再看的音乐剧。美声与通俗的结合,摇滚与古典的跨界,还有众多外形杰出、声音美妙的演员,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剧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片段是Constanze和姐姐Aloysia为了爱情争风吃醋的场景,那首《九泉之下(Six pieds sous terre)》的旋律尤为洗脑,姐姐的高雅霸气和妹妹的灵动娇嗔的演绎让我第一次觉得原来女人“撕逼”竟然能被表现得那么生动活泼,毫无尖酸刻薄之气,反倒显得有些可爱。被姐姐的优秀对比得无颜以对的Constanze爱火攻心地昏了头,直接对Aloysia爆粗口、做鬼脸、吐舌头,惹得姐姐也只好反唇相讥,但两个人又都是出口伤人后懊悔不已,真像一对想和好但不自觉又反其道而行的幼稚园小姑娘。
Six pieds sous terre,这是《九泉之下(Six pieds sous terre)》的网易云音乐链接,有兴趣可以听听看。
此外,音乐剧中莫扎特的经历唤起了我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莫扎特一生颠沛流离,不被世俗看好,遭遇了爱情和事业等种种失败;但他并没有被这个世界磨平了棱角,他的内心依然是像钢一般坚定、像石一般不朽。“挑战陈规,质疑荒谬,唯有癫狂方可前行”,一镜叛逆到底,亲人、爱侣、同侪、生人…… 周遭的一切因子和发生的所有事由似乎都无法撼动他的个性本质。
当时的我,与这样的他还有几分相似之处。我同样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在本该在日光灯下奋笔疾书的日子里我“不务正业”,干着一些与学习无关的事情,漫无目的地寻找着什么。我像呵护珍宝一般呵护着我的个性,使之不会为周遭环境所影响和伤害,所以我宁可任由自己的性子也不愿融入到大环境中。只是我没有勇气和莫扎特一样歇斯底里地反抗外部世界,我只敢在保护好自己人身自由的前提下与环境做最大程度的抗争,让自己的精神得以解放,使自己的人格特质不被磨灭。从应试机器的流水线上频繁逃离,是当时的我一直在尝试做的事情。
下期预告:艺术节演出、和老师对线、图书馆、东野圭吾
- Author:Yuki
- URL:http://shirakoko.xyz/article/writing-02
- Copyright:All articles in this blog, except for special statements, adopt BY-NC-SA agreement. Please indicate the source!
Relate Posts